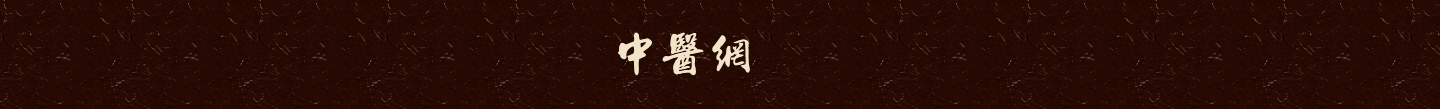知遇之恩与品格垂范忆鲁平同志生存
中药常识 2020年05月05日 浏览:3 次
知遇之恩与品格垂范??忆鲁平同志
鲁平同志是我们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老领导。他是中央制定收回香港、澳门有关方针政策过程的重要参与者,是港澳回归筹备工作的主要操盘手,也是我进入港澳工作领域的引路人。
人生际遇的确有许多偶然。1985年10月前后,我即将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专业研究生班毕业,班主任阴家宝老师告诉我,他与系领导和刑法教研室的几位老师商量后,初定让我留校任教,并表示留校后可以接着读博士研究生。这是许多同学所期望的。我当时少不更事,总觉得自己从一个校门到另一个校门的经历太单一,想换一个环境,去外面的世界闯闯,便婉拒了老师们的一番好意。随后我开始寻找工作单位。考虑到志趣和专业对口等因素,我联系的第一家单位是中纪委,并去官园中纪委大院找了已分配在那里工作的大学同学,对方了解后告诉我中纪委当时还没有从应届毕业研究生中招录的计划。到了次年2月,一天傍晚,我在宿舍床头的小台灯下翻阅当天的《人民》,第4版中间豆腐块大的一则报道吸引了我,标题是《鲁平率领的法律专家小组结束在香港的工作后离港》,文中讲到了这个法律专家小组在香港的一个月内大小座谈会开了上百次。我顿时脑海中闪过一念:香港回归准备工作如此紧锣密鼓,肯定需要大量人手,特别是法律专业的毕业生。于是,我立即给鲁平同志写了一封求职自荐信,并附上自己发表过的几篇文章目录,以平信的方式寄出。
大约隔了不到两周,一天下午,阴家宝老师兴冲冲地到宿舍找我,说国务院港澳办干部处的一位女同志刚刚到学校来了解我的情况,找他谈了话。他复述了与对方交流的过程,讲到如何“狠狠地”把我夸了一通,包括夸赞我的“少年老成”。再过了个把月,之前到学校考察我的李春华同志通知我到港澳办见面。当时的港澳办已从北新桥三条王大人胡同的小院落搬到了永定路东街的一幢四层灰色砖楼内,门口不挂任何牌子,很不显眼。我走进传达室旁边的小房间内,见到了戴着黑框眼镜、形象斯文的徐泽同志。他与我交谈了十几分钟,算是对我的面试。大约5月份,我得到录用通知。这一年是港澳办第一次在北京的高校中招收毕业生,办机关一下子招收了10名,办属港澳研究所也招收了10多人。由于我联系工作单位比较晚,变成港澳办当年招录的最后一名毕业生。
后来我从李春华同志和许崇德老师口中又获知了我被录用的一些细节。许崇德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教授,著名的宪法学专家。他从1985年7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起已开始以委员和法律专家的身份参加起草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那时与鲁平同志已比较熟。鲁平同志在收到我的求职信后,一边厢布置港澳办干部处按组织程序进行考察,另一边厢又委托许崇德老师回人大法律系帮助了解我的情况。许老师此前并不认识我,他到系办公室向几位老师略作打听之后,就回禀鲁平同志,为我说了一番好话。没想到鲁平同志突然问道:小伙子长得怎么样?许老师随口应了一句:长得挺精神的!这一段故事后来许老师曾多次绘声绘色地与我聊起,我们都忍俊不住。他的这句“美丽的谎言”,完全是“护犊”心切,是老师爱护学生的一种本能反应啊!由于工作关系,我后来与许崇德老师以及“四大护法”中的另外三位??肖蔚云、吴建?、邵天任教授来往都比较多,时常向他们讨教,而与我们刑法专业的高铭暄、王作富两位导师反而往来很少,以致香港有的媒体误以为我是许崇德老师的门下弟子。
工作去向确定后,我有一段时间比较多地待在学校图书馆里查阅涉港澳的书刊。所看过的印象最深刻的一本书是香港《快报》曾慧燕小姐所著的《在北京的日日夜夜??中英谈判的我见我闻》。这本书写得很有趣味,不仅记录了追踪中英谈判的过程和花絮,而且介绍了许多相关的人和事。在写到当时任港澳办秘书长兼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秘书长的鲁平同志时,书里有这样一些描述:他反应敏捷,对香港情况掌握准确,令接触过他的人都同声赞好。书中还引述了有的香港人士所讲的一句份量很重的评语:“鲁平是香港人信心的保证。”这句话当时就让我为之震动,我隐约感觉到鲁平同志在香港人心目中的形象和声望超乎寻常,也使我对这位未来的上司在未曾谋面之前已心存敬意。
我进港澳办后被分配在一司一处。这个处主要负责香港情况的综合调研,并配合由外交部主导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有关谈判工作,张良栋同志任副处长,主持全处工作。一司二处负责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的日常工作,徐泽同志是主持工作的副处长。这两块工作都是鲁平同志主抓的重点。入办头两个星期,我们主要是接受以了解港澳基本情况和中央对港澳方针政策为主的入门教育。当时主持港澳办日常工作的是李后副主任,他是一位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过山东《大众》的“老革命”。我至今仍记得他在与我们这批新入办同志座谈时满怀深情地讲过的一番话:你们能参与香港、澳门回归的有关工作是很幸运的。当你年老的时候,你可以自豪地对你的孙子说,爷爷当年曾经参与过收回香港、澳门,曾经为洗刷百年国耻尽了力。人生只要能为国家、为民族做这样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你就可以终生无憾了。这番话让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年轻学子顿时热血沸腾。我所在的一司司长郑伟荣同志在香港出生和长大,曾经担任过廖承志同志的秘书。他向我们介绍中央对港澳的方针政策时,开口就是一个设问句:“‘一国两制’是个什么概念呢?”然后娓娓道来。这种语言风格与我们在课堂里听惯的教学语言大异其趣,也让我一时倍感新鲜。
我第一次见到鲁平同志是上班半个月左右的时候。他当时是从二层的办公室到我们司所在的四层顶楼交代工作,顺便让李春华同志带领他见见我们这批新人。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鲁平同志身材高大,满头银发,前额宽大而高耸,戴着一副老式眼镜,儒雅中透着不凡气度。那天他穿着一件敞领短袖。在逐个和大家握手寒暄后,他就离开了。
参加工作初期的几件小事,让我能切身感受到鲁平同志对我们这些“港澳新兵”的悉心培养。那时我们几乎每天都花不短的时间看香港报纸和杂志。有一天我看到英文版《远东经济评论》中有一篇文章,内容是如何理解和界定行政机关“对立法机关负责”的含义。这是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写到的一句话,对这句话如何在基本法中具体加以规定,当时香港社会出现了争议。该文的作者是时任该杂志、后来成为立法会议员和民主党主席的刘慧卿。我把这篇文章翻译成中文后,处、司领导把译文报送鲁平同志,鲁平同志可能觉得有关观点值得注意或重视,批示编印成港澳办《简报》上报中央领导同志。当时这类简报还是用油墨打印机打印,每年编写的期数并不多,自己从中受到鼓励。还有一次,我在办理公文过程中对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磋商的有关议题提出了一点不同意见,鲁平同志看到后认为问题抓得比较准,打叫我到他办公室去面谈。他说他以前也看到过介绍这个问题的书籍,边说边起身走到书柜前查找。他说的是80年代初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最早翻译的一套丛书,专门系统介绍香港各方面情况和制度。他从中抽出一本,费了好长时间翻阅,直到核对了有关内容为止。1988年春,我和刘强同志作为港澳办第一批先遣人员,被派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下设的国际权利和义务专家小组工作,在跑马地旁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内办公,并在同年7月1日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成立后转入该处工作。不久,李后、鲁平同志率领部分内地起草委员和秘书处工作人员到香港征询社会各界对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意见,我去看望鲁平同志时顺便带了一份报告,主要是建议港澳办驻港书报信息组应把香港各电视台涉及香港基本法起草、中央领导和港澳办负责人有关活动的报道及时录制下来送回北京,并建立音像资料库。当时还没有互联,在北京也看不到无线、亚视等电视台的节目。当天晚上刘振新秘书通知我去取报告,只见鲁平同志在报告上作了一行眉批:“这意见很好!”我当时的感觉是,虽然我们远在香港,但与办领导还是隔得很近。
云南道地药材灯盏花好用吗疾病大全
衡水治疗白癜风医院


-
幸福快乐奥胖评湖人队史先发五虎贾巴尔对不起我是中依依不舍
2020-06-21

-
湖人一战收获未来上个隔扣火箭饼王的叫科比
2020-06-17

-
足浴的保健范围1
2019-07-16

-
刮痧越痛越黑越有效吗
2019-07-15

-
马蛇子的炮制方法
2019-07-15

-
三级中医院评审标准征求意见
2019-0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