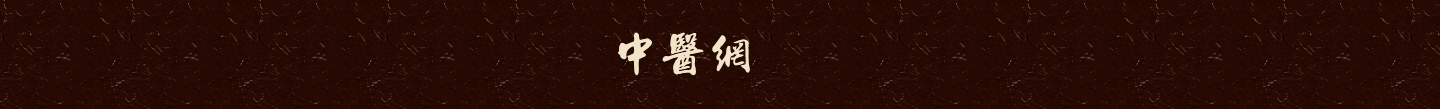藩国作品赏析细节之魅读肖江虹中篇小说犯罪嫌疑
中药常识 2020年07月20日 浏览:2 次
小说简介:故事发生在1976年,龙潭村发生一起花季少女被奸杀的花案。被认为有嫌疑的村小学教师林北(22岁)、骟匠兼麻糖匠王建国( 4岁)、残疾人母光明(72岁)和当过兵的酒麻木胡卫国(4 岁)四人被抓去审问。四人都不承认自己是花案的凶手,花案就此一直悬而未破。而这四人在龙潭村却因此抬不起头,面对村民们的鄙视、嫌弃、疏远和孤立,他们的生活陷入了极其悲剧的境地。最终,他们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纷纷病死,死前却都承认自己是花案的凶手。
这个小说是篇破案题材,却充满浓厚的乡村风土气息。读这个小说,我发现最吸引我的不是它离奇悬迷的故事情节,而是它的乡村事物的细节描写。远去的那个时代的乡村事物在小说中熟悉而又贴心地涌现,把我带入了美好的回忆。
小说中写道:“女人们成群结队去水潭边洗衣服,沿着岸蹲成一排,东家长西家短,也会说些男女之间那些隐秘事儿,于是水面就荡开一片肆意的欢笑。”
我想起我的家乡门口的那条小河流。我年少时,那河水清澈见底,有鱼有虾,一年四季长流不息。每天早晨,村里的妇女们和小妞们都蹲在河边洗衣裳,一派鲜活。我还没起床就能听到满河的捣衣声和欢笑声。
小说中写道:“临时办公地点还没有门,鸡啊狗啊的,文进武出,吼也吼不走,胜似闲庭信步。”
那时的乡村,家家户户都养鸡养猪,猫猫狗狗的也不少。这些家养的禽畜总是围着屋里打转,满屋子拉撒,很是恼人。那时候,要是家里请客有饭局,猫猫狗狗的就耗在桌子下面守嘴,撵也撵不走。要是别家的猫狗也来捡嘴,势必要撕咬起来。
小说中写道:“生产队长两手叉在腰上,模样像要把自己提起来。自从看了《南征北战》,生产队长就爱上了师长这个动作,很革命,很领导,两手一叉,气势恢宏。”
两手叉腰,这个动作在我爷爷那辈特别常见,现在也不落伍,上到国家领袖,下到工厂领班,常见这副架势。女人也有喜欢双手叉腰的,在骂架的时候,往那一站,一个生猛的形象就出来了。两手叉腰,试一下,你还别说,这动作是有那么一点玩味。
小说中写道:“老太婆往锅里舀了小半瓢油,回头看见肖明亮,慌忙舀出一些放回油碗里。生产队长对着领导家属和颜悦色地挥挥手,老太婆立化刻堆满笑,重新把舀出来的油倒进锅里。”
这里说的油应该是菜籽油了。菜籽油炒菜特别香,蒸饭也很美味。但是那年代,物质匮乏,油都是很省着用的,毕竟一大家子好几双嘴,日子又长又瘦的。
小说中写道:“老娘把面条端上桌,反身给儿子撬来一坨白亮亮的猪油。刚转身,林北把还没有融化的猪油挑出来塞进了老娘的碗底。老娘坐下来,把面条搅拌搅拌,-3,654碗底成了大庆油田,油珠子争先恐后往上冒。
说到猪油,它跟菜籽油一样也是那时候的常用食用油。猪油主要煮汤用,炒饭特别香。然,猪油比菜籽油珍贵,那可是猪肉熬出来的,一斤猪肉四块多钱,熬不了多少猪油来,再说,一个月又能吃上几顿荤呢。
小说中写道:“黑板也不行了,漆全脱了,都成白板了。粉笔也不够用,五个老师一个学期就十盒粉笔,写到手都捉不住了也舍不得丢。”
粉笔,那可是老师的专用,黑板白字,讲台上下都是灰。那时读小学,最喜欢值日擦黑板。擦黑板有一种蹂躏的快感,擦,擦,擦,擦不够就跳起来擦,擦得粉笔灰落了一身。当然,我也喜欢粉笔,喜欢放学后在讲台上寻觅一番(一般放学了,老师都把粉笔盒带走,打粉笔主意的同学太多了)。我家的门上,墙上,水泥地上都有我和弟弟天马行空的表达。
小说中写道:“一大早,老把的院子里就聚满了人,堂屋的神翕前摆着一副白棺材。按照龙潭村的规矩,没出阁的闺女是不能用黑漆棺材下葬的。棺材是椿木的,老把本来是给自己准备的,说等过万象函归方丈室完年就请漆匠过来上漆的。命啊!”
治丧,也叫白喜事。对于死者,棺材是有讲究的,老人才够得上用黑漆棺材,年纪轻的只能用白棺。用白棺只能得到人们的叹息。老人以用黑漆棺材为荣。那时的丧事办得很真,但也很磨人。
小说中写道:“林北走进院子里,老娘正在窖酸菜。把绿油油的青菜摘回来,洗净,放进滚烫的开水里跑一圈,捞起来。等凉透了,塞进封釉的坛子,倒进半碗老酸汤,六七天就能吃上嘎巴脆的老酸菜。”
我妈妈也会窖酸菜,与这里的做法几乎一样。青菜可以是小白菜秧子,也可以是白萝卜秧子。白萝卜秧子窖的酸菜最好吃,也最下饭。
小说中写道:“叶片上的露水还没有被太阳烘干,接电影的就回来了,沿着石板路一路高喊:干仗的,铁道游击队。干仗的,铁道游击队。人们奔走相告,开始重新安排今天的生活,晚饭是一定要早的,除了爹妈跷脚,再重要的事情都要摞下。孩子们更是早早就把小板凳夹在腋下,连吃饭都舍不得放下来。草草扒完两碗饭,人流就开始往晒谷场去了,先来的精心挑选一个好位置,晚来的只能退到晒谷场后面的斜坡上,不过听不见怨言,一派的欢欣鼓舞。”
赶电影,那可是乡下的大开心事,别说小孩,大人都激动不已。不过,我们那时赶电影,得盼人家办喜事。只要听说谁家有喜事,就四下打听有没有电影看,是什么电影,然后奔走相告。晚饭一吃,落了一锅花生或是蚕豆揣兜里,出门。遇上邻村放电影,只要不是很远,我们也会去赶场子,天一擦黑就带了手电筒,约好伙伴一起。看完电影又一起回家,夜晚一起走在路上说说笑笑,一点害怕的心理都没有。
小说中写道:“滴答,滴答,/下雨啦,下雨啦。/麦苗说:‘下吧,下吧,我要长大。’/桃树说:‘下吧,下吧,我要开花。’/葵花子说:‘下吧,下吧,我要发芽。’/小弟弟说:‘下吧,下吧,我要种瓜。’/滴答,滴答,下雨啦,下雨啦。/”
好熟悉的文字!这分明是我上小学时一年级的语文课文嘛。我九二年开始上学,那时读书的孩子真多,小学校园真是热闹。小说中还提到《数星星的孩子》、《骄傲的孔雀》、《乌鸦喝水》等课文,我都很熟悉。那时的语文课本现在想来真是觉得经典,在我下一届却改版了,改成了插图卡通的版本。我弟弟低我一届,他跟我学的于是就很有差异,我甚至就此认为这就是我们在玩的方面有些玩不到一起去的原因。
小说中写道:“抹了一把脸,王建国端条凳子往桌子后一坐,锤子和錾子敲得叮当响,一脸红光地唱起了《麻糖歌》。”
麻糖好吃。好些年没见到有人走村串户卖麻糖了。那时,只要听到锤子和錾子敲打的声音以及卖麻糖的吆喝声,我和弟弟就赶紧在屋里翻找旧拖鞋废胶什么的,这可是换麻糖的好东西。所以,那时穿旧穿破的鞋子是舍不得扔的,得攒起来,等卖麻糖的一来,就拿去换麻糖吃。
小说中写道:“最抢眼的就是那些哺乳期的女人们了,怀里搂个嫩苔苔,屁股挂在晒谷场边的石凳上,撩开上衣,拉出白花花的 就开始喂奶。”
小时候,吃奶,现在还真不记得是什么味了。我带过小孩,小孩好吮吸,给他一个手指头,他也能叭嗒叭嗒吮得津津有味。我们那一代的小孩是幸福的,吃母乳,一直到长牙齿。那时的母性是伟大的,孩子饿了,旁若无人地喂。
小说中写道:“他从箱子里取出骟猪刀抹了抹,主人家端来一盏油灯,骟猪匠把刀子放在火焰上过了几道,一只手捞起猪崽两个蛋蛋,骟猪刀轻轻一抹,一带,一扣,就攥住了两粒雪白。把两颗蛋蛋递给主人家,王建国呵呵笑着说,加一把芹菜,就能炒一盘味道鲜美的猪卵蛋了。”
我们村里也有一个骟匠,论辈分我还得喊他伯伯。平时常看见他路过我家门口,早出晚归的。他的骟活技术很好,不但骟猪,还骟鸡仔。被骟的那些禽畜在他手里,几声惨叫过去,走路先是有点歪,不过几天就活蹦乱跳了。他也是个兽医,技术闻名邻近好几个村子。如今老了,他儿子又承传了他的行当。
小说中写道:“晒谷场边有几架风簸,风簸是用来扬稻谷的。一人来高,顶上一个大豁口,底下两个出谷口。扬谷的时候,先把卡子卡死,把晒干的稻谷倒进大豁口,手把着卡子,慢慢把谷子放下来,手摇动扇叶,一架风簸就风起云涌了。秕谷和尘土从风簸后面的出口飞扬而去,沉甸饱满的谷子就滑进下面的箩筐。”
风簸,我家也有一个,至今还在用。风簸不但扬谷子,还扬麦子大米黄豆之类。那是个好工具,我甚至可以把它当风扇用。我和弟弟一个摇,一个站在出风口,风从风簸里跑出来,吹凉了夏天。
小说读完了,有点恋恋不舍,而我还沉浸在回忆中。那些美好的乡村事物很多很多,而小说中出现的只是其中一角,对于小说,已经到位了,也已经足够把我的深处记忆翻松,翻醒。
这个小说没有华丽的语言表达,而在细节描写上却大放异彩,清晰而有画面质感地还原了醇厚乡土的那个黑白胶卷年代的人与事。我也这才发现,小说,原来细节更能动人心弦,细节也可以魅力无限。而作者在创作谈中也说:“小说最大的挑战不是主题,不是结构,不是语言,而是细节。情节只能组成小说的骨架,细节才是小说的血肉。”
共 475 字 1 页 转到页 【编者按】其实,这篇文算不得真正的评文,说读书随感或许更为确切。但作者倾心于文字中的这一份惬意,才是真正令人心醉之处,更是作者之幸。同时,作者别取蹊径,随读随感,亦不失为一种值得推崇的读文之法。----累了请抽支烟
1楼文友: 08: :01 欣赏了,遥祝创作快乐! 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文学联合协会会员 ,作品散见于中国诗歌流派《诗歌周刊》,《参花》,《三晋诗韵》,《江山文学》《西部作家》等杂志和络。
2楼文友: 22:50:55 我这是第二遍看,觉得文字很有深度 甜到忧伤
楼文友: 00:10:24 感谢的精彩点评,以及各位文友的到访和赐教,祝愿大家共同进步。
4楼文友: -07 12:17:09 情节只能组成小说的骨架,细节才是小说的血肉!经典,学习啦,谢谢 吾手写本心 结交同路人
湛江白癜风医院哪种药治疗灰指甲好使淮安白癜病医院
- 上一篇: 藩国末字怎样组词
- 下一篇 藩国贾樟柯剧本完全依靠网络文学不现实

-
幸福快乐奥胖评湖人队史先发五虎贾巴尔对不起我是中依依不舍
2020-06-21

-
湖人一战收获未来上个隔扣火箭饼王的叫科比
2020-06-17

-
足浴的保健范围1
2019-07-16

-
刮痧越痛越黑越有效吗
2019-07-15

-
马蛇子的炮制方法
2019-07-15

-
三级中医院评审标准征求意见
2019-07-13